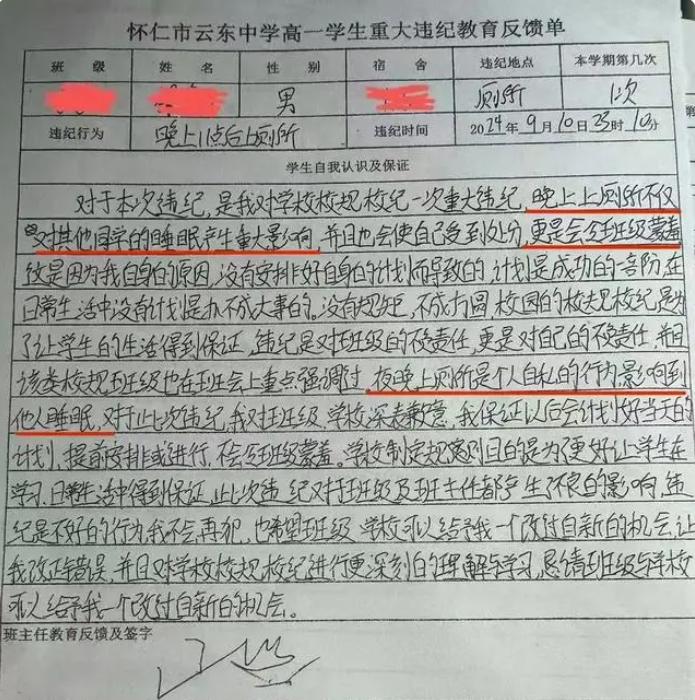摆脱社会化的学生思维
前天录了期博客,把「AI会不会毁灭人类」的大主题里的「人」的部分给解决了——即AI会不会毁人类的思考能力。
在聊的内容中,提到了「学生思维」这件事,想想还有值得拓展的有趣部分。
首先,我需要明确一个态度,学生思维并没有「不好」,只是人们习惯性地用「更高一级」的东西来证明自己所在的层级是「正确的」,所以才需要分出层级问题。但是不得不否认的是,透过认知层级分立的阶级歧视是实际存在的,所以很有可能当我们提到「学生思维」,对于学生思维而言就像是找到了参照物去证明它是「错误的」。
其次,学生思维却又是每个人必须要经历的阶段。无论你是否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人的认知体系本身就需要经历理解对与错、寻找标准答案、碎片化知识构建自身知识体系的过程。
最后,才需要讨论学生思维向其他思维转变的途径。甚至在功利主义的视角里,学生思维带来的正向反馈远远超过独立思考,那是否要转变学生思维,就成了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
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存在标准答案?
学生思维最大的惯性思维,便是在寻找「标准答案」。在播客开录之初,我们请过朋友来录制节目。她是一个每天都在「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的人,所以我们从她的表象开始慢慢拆解,找到了焦虑症、正向反馈依赖的底层逻辑。于是她直接跳到了最后一步:那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对了,她的职业竟然是一个支行的银行行长。学生思维并不会因为当事人所处的社会结构而自动调整——因为标准答案就意味着「正确」,可以避免更多的时间被浪费在无用的「过程」上面。
但当学生思维无法寻找到「正确答案」,甚至是知道自己无法做出结果时,又会受困于「过程」。我刚入职社会那几年,最爱干的事情就是「做笔记」,开会的时候我的笔记详尽到每一次会议纪要都得我来写然后抄送全部门。那段时间一直在做「助理」的工作,所以几乎我的所有工作都是「被安排」的,有些安排甚至会给到我明确的「结果指标」,这种感觉会让人上瘾,就像每一个赛段的奖励一样,可以不断地得到正向反馈。
然后有一天,我的主管告诉我要做一本机载杂志的刊例价,我依旧按照过去的逻辑,端着笔记本准备认真一条一条记录「标准答案」时,他告诉我这一次由我自己随便做,没有任何要求。
「你总得给我一个模板,让我知道刊例价的定价吧?」
「价格的部分先空着。」
「但是我不知道哪些地方可以投放广告啊?」
「我也不知道,所以需要你去了解。」
「找谁?」
「你开了这么多会,记了这么多笔记,你也应该知道每个部门在做什么事吧。」
我怎么知道我做对了?
当我把刊例价的PPT交给主管时,他看了一遍,才让我去做了「标准答案」的事情,他让我去看看其他航司的刊例价报价,然后让我去思考支线航空的广告投放应该如何定价。
对,他当下竟然没有反馈我的刊例价PPT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再之后,就看见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大致是说:这次自己带进来的「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不用当「学生」教,希望那家伙看到这条朋友圈不要对号入座不要骄傲。
这对我来说就是当初最想得到的「正向反馈」,所以我还是手贱回复了「是在说我吗?」他回复我「老子说了不要对号入座。」
大致就是这个节点之后,部门大部分事情都是我直接处理,不再是助理身份去完成被安排了「标准答案」的工作。
虽然这个故事有点装逼,但装一下我本身也是写博客的功能性之一。但确实是那一次事件之后,我的正向反馈阈值被提高了很多——如果我们把脱离「学生思维」比喻成发射至外太空的火箭,正向反馈的切换是,在另一层高度围绕地球圆周运动的第一宇宙速度,即:
- 当可以做出「结果」时,标准答案即「正向反馈」;
- 当无法做出「结果」时,过程努力即对自我满足的「正向反馈」;
- 当「标准答案」不存在时,「仪式感」即对自我满足的「正向反馈」;
我特别提到「自我满足」这件事,是因为当我开始做主管的时候,从另一个视角理解了「学生思维」。
父与子
当爹的乐趣,是因为有一个听话的孩子。学生思维是非常好的「子」,可以承载大部分人在当爹时的操控欲和说教欲——所以,当我开始做主管的时候,当爹的乐趣也一下子体会到了。
所谓的「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如同白纸一样」,表象说的是他们肯学好教,潜台词其实说的是他们「好控制」。还在大厂工作那会,我们倒是有了独立的能力,所以把项目争取独立之后,便开始招聘自己的员工。学生思维的新员工,总是会体现出「好学」的样子,所以安排工作相对来说容易很多——但就是这种「容易」很容易发生「没结果」的情况。
职场是一个讲「结果主义」的地方,能够做出结果看上去是一个「标准答案」,但它追加了很多「说服他人」的要求,而不是自娱自乐地「我最近把周数据表格增加了一个栏目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数据变化」来体现工作能力。
但当结果无法达成时,「努力」就成了一个很容易自我满足的模块。比如加班到晚上10点,如果出公司写字楼不拍一张证明加班的照片,这个班就加得毫无意义——但与之相对的,是「结果」在哪里?如果加班能带来结果,是否它就已经作为邮件附件,抄送给了「能够看见你努力结果」的部门了?而不是变成了一张「天啊,我好努力」的朋友圈。
但这件事没办法被直接戳穿,所以这种粉红泡泡一般会在最后一刻才被戳爆——
「结果呢?」
「我做了这些努力。」
「然后呢?结果呢?」
然后对方开始给我展示他的文件整理归档得有多细致、表格排版有多细心、产品原型像素对得有多齐、代码写得多漂亮,但就是没有「结果」。
是不是有一种父与子的乐趣?我告诉你,这件事是会上瘾的,无论是习惯性说教的「爹」,还是以学生思维惯性思考的「儿子」。因为被「说教」就意味着知道了接下来「我该怎么做」的方法论,就算没有做出结果,「说教者」还会手把手地教会解题思路,然后变成笔记本里一条被精心珍藏的「公式」。
显然,职场没有「知识」,它必然由「经验」构成,所以犯错也是必然的。所以学生思维容易在「犯错」之后去追求「正确答案」,但经验主义者则需要提供当下的「解决方案」,并形成未来SOP里的重要环节,这便是脱离地球引力(即爹引力)的第二宇宙速度。
扔掉笔记
当我们开始自己工作时,有意识地开始克制享受当「爹」的乐趣,便提出了另一种对学生思维的要求——有问题就问。
很显然,问问题是「认知」领域的事情,而不是「方法论」。就像是小学大家还会积极举手,到青春期之后,别说提问了,回答问题的人也开始越来越少。成年后,问问题有很多情况是「预设了答案」而问的,比如我希望权威看见我、或是我希望所谓的权威掉进我提前预设的逻辑陷阱从而体现我超越权威的能力。
前几年,老婆开过线上的塔罗课、占星课,当时会让跟我们关系比较好的徒弟来家里上课。每一次到需要他们实操占卜时,有的徒弟无时无刻都需要借助笔记解牌。最后一堂课,她给了几个徒弟最后的「时限」,如果准备好了要开始实操练习了,就把笔记扔掉,或是交给我们统一处理,否则永远都迈不出实操的那一步。
期间我们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让徒弟挨个录制塔罗的周运势视频,渐渐地也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差距,从他们的表述其实能非常明显地看到谁是在照本宣科地使用「笔记」。学生时代,我们之所以要做笔记,是因为零散的知识点需要通过整合的方式形成「解题思路」,但为什么有的学生会卡在数学应用题的最后两题,是因为这些知识自始至终都是零散的,所以需要整合的时候,就看出了学生思维里「知识依赖」的局限性。
成年人,或者说是进入社会的成年人,开始拥有模块式的学习能力,会在接受到一个全新知识时,有意识地进行知识整合,放进不同的「待用」空间。这一点和学生思维的「整理零散」知识的本质区别,在于你是否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而这套系统并不会因为年纪、职位得到自动优化。
所以,很多人卡在了社会化学生思维转变的夹缝中,一旦意识到「正确答案」不存在时,就会本能地逃回那些「努力」和「仪式感」之中,通过自我满足的方式,来获得短暂路径的正向反馈。
这点没错,只是它会随着「任务难度」提高而变得越来越内耗。
一旦回到问题本身,开始试着寻找「为什么」的时候,学生思维就开始有了一层向独立思维蜕变的伊始。这便是脱离太阳系引力的第三宇宙速度——扔掉知识、整合知识与经验、然后开始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到底有没有正向反馈?
如果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独立思考确实很难有价值上的正向反馈,但同时独立思考可能追求的「正向反馈」其实本身就脱离了学生思维的那种快速路径。
这个话题留到之后再聊——因为独立思考似乎也不会全然地带来「好事」。